■ 卞王玉玨
從新華南路7號到金盤路30號,從最初的兩層小樓到如今高達二十一層的大廈。這不是簡單的位置轉換,它記錄著《海南日報》的一路風雨一路歌。尤為榮幸的是,在這巨大的發展變遷中,有我踏足其間留下的淺淺腳印,那由遠而近的腳步聲,輕輕地訴說著我和《海南日報》的深厚情緣。
歲月悠悠,屈指數來,至今我與《海南日報》結緣已有三十七個年頭。上世紀80年代末,在通什(今五指山市)讀書的我,因仰慕“鐵肩擔道義,妙筆著文章”的記者,深深地愛上了新聞寫作,成為了學校廣播站的特約記者。課余時間經常在校內外采訪,除了給校內供稿外,還給省級報社電臺投稿,《海南日報》就是我投稿的省級媒體之一。我清楚地記得,當時的新聞稿件都是通過郵寄的方式投遞,“海口市新華南路7號”這一投寄地址至今還深深地烙印在腦海之中,久久不能忘懷。那時候,每一篇稿件的投出都寄托著一位懵懂少年的期望,當小小的豆腐塊見諸報端時,我會高興好一陣子。從1988年至1990年,多篇新聞稿件陸續在《海南日報》刊發,使我成為了小有名氣的校園記者。
1990年9月,我踏入原瓊臺師范學校就讀后,離新華南路7號更近了。這時期,當我了解到該校書法教學成績顯著時,立即采寫了一篇題為《瓊臺師范學校書法教學卓有成效》的消息稿,并一路打聽,親自把稿件送到報社二樓編輯部。本來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投稿,沒想到,兩天后,我的文字變成了鉛字。捧著當天的《海南日報》,聞吸著淡淡的墨香味,我激動得振臂歡慶。正是《海南日報》編輯的支持和幫助,使我更加堅定了對新聞寫作的熱愛,直到走上工作崗位,仍孜孜以求。借助《海南日報》這方發表天地,我的寫作水平和個人事業得到了不斷提升。
1997年5月,通過參加公開招考,我成為了東方市廣播電視臺的編輯、記者,踏上了新聞從業道路。從此,與《海南日報》駐東方站記者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,我經常向他們提供新聞素材,合作發送稿件,向外界宣傳推介東方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。
2002年2月,通過公務員考試,我調入東方市委辦公室工作,成為了市委新聞秘書、《海南日報》特約記者,與《海南日報》的關系更加密切。在隨后的十年時間里,我和報社記者并肩“戰斗”,奔波于鄉鎮村莊、機關社區采訪,一篇篇新聞稿件陸續在《海南日報》發表。其中,《燃起激情跟黨走》《新興工業領跑東方經濟》等頭版頭條新聞,更是得到了各界的肯定。其間,《海南日報》不斷改版擴版,版式越來越美,影響力越來越大。作為基層一線記者,我為此感到高興和自豪。2004年7月6日,海南日報報業集團正式掛牌成立,從單一的《海南日報》發展成了海南經濟特區傳媒巨頭。我也與海南日報一同成長,從市委辦科員晉升為副主任科員,直到主任科員、辦公室負責人,市委宣傳部副部長、市廣播電視臺臺長等職。可以說,海南日報社是我成長道路上的“貴人”,我早已把它當作自己的家,把報社領導、編輯、記者當成了家人。一路走來,我和一撥撥駐東方站記者友好相處、風雨同舟,建立了親密的戰友關系。這中間有苦也有樂,有喜亦有悲。最令人痛心的是,2004年9月4日,我敬仰的兄長甘遠志同志在東方采訪途中因心臟病突發,不幸倒在了他熱愛的工作崗位上。當時,我目睹了他在醫院被搶救的全過程。當噩耗傳來,猶如當頭一棒,我心如刀絞,簡直不敢相信剛剛還有說有笑的一個大活人,轉瞬間竟然與我陰陽相隔。悲傷中的我飽含淚水寫下了通訊稿《他倒在了自己熱愛的崗位上——追憶海南日報記者甘遠志生命的最后時刻》,發表于9月8日《海南日報》頭版,向他做最后的告別。
后來,因為工作需要,我離開了新聞宣傳工作崗位,但依然與《海南日報》保持著密切的來往。從2011年開始,我的多篇散文作品先后在《海南日報》文化周刊椰風版或海南周刊隨筆版發表。她見證了我從一名新聞工作者轉變為基層作家的過程。今生與《海南日報》的情緣已無法割舍,她將陪伴我度過余生,我也將為她的發展默默鼓勁加油。
5月7日,《海南日報》迎來創刊七十五周年大喜日子,3月的某一天,我沐浴著春日的暖陽,再一次回到心心念念的金盤路30號。仰望海南日報報業集團大廈,凝視著全國優秀記者的楷模甘遠志同志的雕像,那些激情澎湃的歲月又一幕幕清晰地呈現在眼前。駐足其間,我陷入了深深的感懷之中。
您訪問的鏈接即將離開“海南省人民政府”門戶網站
是否繼續?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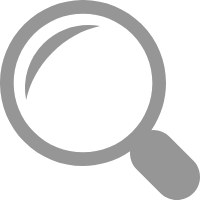

 瓊公網安備 46010802000004號
瓊公網安備 46010802000004號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