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97年盛夏,年過花甲的蘇軾,在兒子蘇過的陪伴下,渡過瓊州海峽,來到海南。在這里,蘇軾度過了虎年、兔年、龍年三個(gè)春節(jié)。
北宋紹圣五年(1098年)是個(gè)虎年,蘇軾第一次在儋州過春節(jié)。這個(gè)春節(jié)的關(guān)鍵詞是“孤單”。節(jié)前的臘月二十七,蘇軾一夜沒睡。燈芯已經(jīng)燒焦掉落,他無心將它挑亮,只有爐里的香薰,蘇軾時(shí)時(shí)去撥動(dòng),香雖然已經(jīng)燃盡,室內(nèi)還彌漫著香氛。
佳節(jié)思親,他想到自己和兄弟蘇轍,一個(gè)在儋州,一個(gè)在雷州,離家?guī)浊Ю铮恢裁磿r(shí)候才能回還。于是,他寫下了《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(dá)曉寄子由》:“閉眼此心新活計(jì),隨身孤影舊知聞。雷州別駕應(yīng)危坐,跨海幽光與子分。”
這年的上元(元宵節(jié))之夜,儋州地方官員舉行上元招待會,邀請各界名人參加。可能是因?yàn)樗槐怀⒋髥T待見,儋州的官員不想惹這個(gè)是非,也可能是他自己主動(dòng)避嫌,所以他本人沒有出席,只讓他的兒子蘇過代為參加。
這段往事被蘇軾記錄在《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(dú)坐有感(戊寅歲)》中,只有56個(gè)字,但細(xì)節(jié)很足。
1099年,蘇東坡的兔年春節(jié)關(guān)鍵詞是“友情”。
正月十三日,儋州大地終于迎來一場春雨,雨量雖然不大,但也能解一時(shí)的旱情。與這場雨一同拜訪蘇軾的,還有來自內(nèi)地的信件和包裹。
他打開包裹,看到里面是一大包柴胡,還有在儋州極難找到的藥品。初春時(shí)節(jié)容易傷風(fēng)感冒,柴胡有大用場,蘇軾非常感動(dòng)。
兩天后是正月十五。與一年前相比,蘇軾交了很多本地朋友,不必再獨(dú)掩門扉,在無聊的等待中度過上元節(jié)了。這天晚上,有幾位與蘇軾年齡相仿的老書生,相約來到蘇軾家,邀請他趁著月色出游:“良月佳夜,先生能一出乎?”蘇軾求之不得,欣然同行。
他們走進(jìn)僧舍,又穿過一條條小巷。街上百姓來來往往,賣肉的、賣酒的各色生意人紛紛攘攘。回去的路上,他邊走、邊想、邊笑,到家的時(shí)候,已經(jīng)敲過三更鼓了。
1100年,龍年,是蘇軾在海南過的第三個(gè)春節(jié),關(guān)鍵詞是“紅火”。
蘇軾擔(dān)任的是“不得簽書公事”的虛職,空閑時(shí)間很多。在海南的時(shí)間一長,對人情與物產(chǎn)逐漸熟悉,他琢磨起制作“海南墨”來。按蘇軾的說法:“海南多松,松多故煤富,煤富故有擇也。”他在住所旁邊搭建了一個(gè)“墨灶”,點(diǎn)燃松枝,獲取煙灰。年前的臘月二十三晚上,燃燒的松枝火焰外溢,點(diǎn)燃了墨灶,火越燒越大,幾乎蔓延到旁邊的住宅。蘇軾和兒子趕忙取水滅火,好一頓忙活才將火撲滅。
龍年春節(jié)就這樣紅紅火火地拉開了序幕。經(jīng)過這一事件后,蘇軾不再制墨。但余下的松明足足有一車,正好可以在春節(jié)期間照明。臘月二十八,蘇軾寫了《夜燒松明火》:“夜燒松明火,照室紅龍鸞。快焰初煌煌,碧煙稍團(tuán)團(tuán)。”在這首詩中,蘇軾還提到:“坐看十八公,俯仰灰燼殘。”十八公引出了另外一個(gè)故事,原來,在海南,蘇軾得到了一組十八羅漢的畫像,蘇軾非常喜歡,讓人重新裝裱、點(diǎn)燈設(shè)香供奉。松明火,也照亮了他的羅漢像。
他的一顆心也是火熱的。在外多年,蘇軾仍然關(guān)注著朝廷的大事。這一年的人日(正月初七),他聽說頻繁改道的黃河已恢復(fù)北流,多年的治河之爭遂告終結(jié)。于是寫下《庚辰歲人日作,時(shí)聞黃河已復(fù)北流,老臣舊數(shù)論此,今斯言乃驗(yàn)二首》,其中既有對黃河安寧的欣慰,也有自己安于避居海南的表白。此時(shí),他對海南的風(fēng)物,已產(chǎn)生了感情,首先是“檳榔生子竹生孫”,蘇軾自注說:“海南勒竹(簕竹),每節(jié)生枝如竹竿大,蓋竹孫也。”他還喜歡漫步在儋州田野:“春水蘆根看鶴立,夕陽楓葉見鴉翻。”
小日子也過得火火熱熱。正月十二,他自釀的天門冬酒熟了,壇蓋一開,清香就飄散開來:“天門冬熟新年喜,曲米春香并舍聞。”蘇軾很高興,他一邊將酒過濾(漉酒),一邊忍不住喝起來,嘗著嘗著就醉了。好在這是在家里,可以倒頭就睡:“醉鄉(xiāng)杳杳誰同夢,睡息齁齁得自聞。”
這年的二月,朝廷詔令蘇軾移廉州(今廣西合浦)安置,蘇軾辭別生活了近三年、度過三個(gè)春節(jié)的海南。(紀(jì)習(xí)尚)
您訪問的鏈接即將離開“海南省人民政府”門戶網(wǎng)站
是否繼續(xù)?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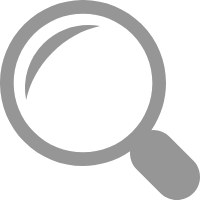

 瓊公網(wǎng)安備 46010802000004號
瓊公網(wǎng)安備 46010802000004號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