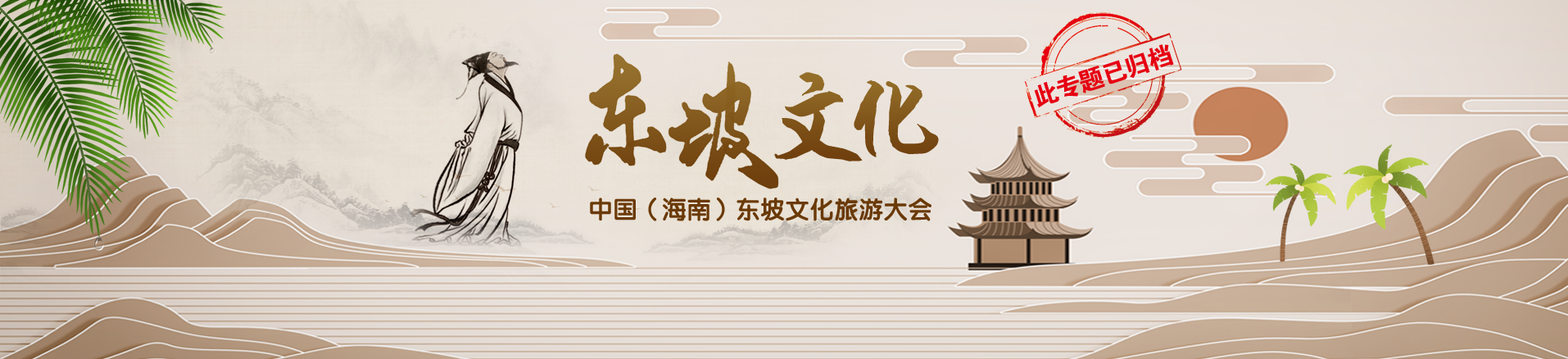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:
一尊還酹江月

趙孟頫筆下的東坡形象。資料圖
阮忠
黃州,是蘇東坡自稱人生功業所在地之一,地因人彰顯,也因文名揚,惠州、儋州也是如此。黃州瀕臨長江,有一地人稱“赤壁”。東坡因“烏臺詩案”被貶后,在宋神宗元豐三年(1080年)二月到黃州任團練副使;元豐七年(1084年)四月改任汝州團練副使,離開黃州。四年間,他多次來過赤壁,留下“二賦一詞”(即《前赤壁賦》《后赤壁賦》和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詞),讓黃州名滿天下。我們今天要談的是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。
詞入北宋漸興,名家輩出,詞的風格也更加多樣化。晚唐溫庭筠后,“花間詞”的柔婉輕媚成為詞壇風氣,人們以詞為“艷科”,多表現男女情戀、相思離別,是尊前、月下、花間之物。但是,到了北宋歐陽修時,詞風漸有放達,至東坡時,詞風又生豪放,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。全詞如下:
“大江東去,浪淘盡,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,人道是,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穿空,驚濤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,一時多少豪杰。
遙想公瑾當年,小喬初嫁了,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,談笑間,檣櫓(一作強虜)灰飛煙滅。故國神游,多情應笑我,早生華發,人生如夢,一尊還酹江月。”
這首詞豪放,起勢不凡。在“大江東去”的自然狀態中,江水滔滔,給東坡的感覺是長江奔涌的浪花,淘盡了千古風流人物。他心潮起伏,以這句詞道盡了過往世事滄桑。那東去的長江水,暗喻了無情的時光。逝者如斯,千古風流人物不再,而大江仍然東流,浪花依舊怒放。
東坡有感而發,“故壘西邊”人們所說的“周郎赤壁”是這首詞懷古的立足點。應該說明的是,“三國周郎赤壁”究竟在哪里,后人一直眾說紛紜,東坡時此事就有爭議。因此,東坡也疑惑黃州“赤壁”不是三國赤壁大戰發生地的“赤壁”,故借“人道是”發思古幽情。“亂石穿空,驚濤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“江山如畫”沒變,但古時的赤壁豪杰何在?物是人非,如今唯有他孤獨地站在江邊享受清風明月。
此時,東坡腦海里浮現出三國時,吳國周公瑾大敗曹操八十萬大軍的情景。明代羅貫中在《三國演義》中,用近十萬字繪聲繪色地描述了諸葛亮草船借箭、借東風,周郎火燒曹營及曹操敗走華容道的故事。東坡在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這首詞中只說主帥周公瑾。公瑾娶小喬、戰曹操,羽扇綸巾的神態與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功業,盡顯他的人生得志、意氣風發。周公瑾當年34歲,這讓東坡想到自己40多歲鬢發花白,功業何在,內心情緒從豪放轉為沉郁,以結句“人生如夢,一尊還酹江月”感慨自我壯志未酬,悵惘難以言說。
這首詞一唱三嘆,寄情高遠,后人贊為古今絕唱,無赤壁詩詞能夠超越。